作者:xumingdaren
2025年8月7日发表于第一会所
本站首发
字数:12257
金老板这个大变态非让我们写自己被轮的经历,还说必有重赏,这招是真他
妈毒啊。
我窝在沙发上,跷着大长腿,一目十行地刷着小骚慕和小圆妹妹那两篇所谓
的「轮奸自传」,差点没把嘴里的红酒喷到电脑屏幕上。
不就是被一帮男人轮着干了吗?瞧她们写的,开篇那叫一个委屈,那叫一个
惨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贞洁烈女失身实录。
搞了半天,看到最后不也一个个爽得哼哼唧唧,找不着北了?
特别是小圆那老妹,非得把过程写得跟受刑似的,现在不也成了个小魅魔,
提起男人那点事比谁都门儿清。
就因为她们俩开了这个头,后来总有烦人的拐弯抹角地跑来问我:「楠姐,
你呢?你第一次被轮是啥体验啊?」
我能有什么感觉?
非要说第一次,那得追溯到初中。你还别不信,就是初中。不过那次真算不
上什么,就跟几个差不多大的辍学小混混瞎胡闹,毛都没长齐,懂个锤子。说是
轮,其实跟小孩过家家没区别,我当时甚至觉得有点无聊。
真正让我觉得栽了,倒霉到家的,刻骨铭心的,就要属那一刺了。
靠,要不是为了金老板那笔丰厚的赏金,这件事我宁愿烂在肚子里,带进棺
材里,这辈子都不会跟第二个人讲。
记得,大概是大二下学期吧,那时候小骚慕还在宿舍里抱着言情小说做情种
梦呢。而我,早就是道外区那片公认的头牌了,价高且活儿绝对好,点我的人能
从街头排到巷尾。
可惜,摊上个不做人的鸡头,雁过拔毛都算客气的,他那是直接把雁抓来炖
汤。我累死累活一晚上,他张嘴就抽走七成,还舔着脸说是「管理费」和「保护
费」。
保护我?上次有个客人喝多了想动粗,他妈的跑得比兔子都快。
我寻思着,这钱我自己躺着就能挣,凭什么分给他?
于是,我一脚踹了那孙子,决定单干。
当楼凤,自由,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
单干的第一步,就是找个合适的窝。
江北那个新小区,我一眼就相中了。
安保号称江北区第一,进出刷脸,陌生访客盘查得跟审犯人似的,完美。最
重要的是,入住率不高,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没人会多管闲事。
我租了个八十平的两室一厅。一室一厅怎么够用?小姐姐我自己住一间,
「上班」用一间,公私分明,这叫专业。
接下来就是砸钱。我花了几乎一半积蓄,把这地方彻彻底底改造成了我的专
属「情趣屋」。
客厅的主色调是暧昧的粉和紫,一张巨大的天鹅绒软沙发陷在中央,客人一
进来就能融入其中。次卧我自己住,没什么花哨,简单舒服就行。
真正的重头戏在主卧。
那张智能恒温水床是我托人从国外订的,光运费就够普通人一月工资了。天
花板上镶了整面的镜子,三百六十度无死角,能让任何男人在上面找回雄风的快
感。
连接着主卧的浴室,我丧心病狂地把墙敲了,换成了全透明的钢化玻璃。里
面是双人雨林花洒,水汽氤氲间,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
衣柜里更是我的军火库,各式各样的「战袍」挂得满满当当。布料少得可怜,
遮住的还没露出来的多,但效果嘛,懂的都懂。旁边的小抽屉里,手铐、眼罩、
小皮鞭……琳琅满目,能满足客人的所有幻想。
整个屋子都装了智能系统,灯光、音乐、香氛,我拿着手机就能一键切换。
想玩清纯学生妹,就来点柔光配轻音乐;想当性感女教师,那就红光配爵士乐。
看着这个完全由我掌控的王国,我心里那叫一个舒坦。去他妈的管理费,去
他妈的保护费!从今天起,老娘赚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属于我自己。
万事俱备,只欠客户上门了,嘎嘎。
而事实证明,姐姐我单干的决定英明神武。
靠着「附近的人」和我精心装点的情趣屋,我手机里的客户列表一天比一天
长,微信到账的提示音成了我最爱听的爽嗨音。
不到半个月,我就积攒了好几个出手大方的回头客,赚的钱比跟着那孙子干
半年都多。
这天早上,我刚送走一个活儿好话不多的小富二代,正美滋滋地躺在床上,
盘算着这个月能攒下多少钱。
就在这时,一阵「嗡嗡嗡」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响起,像是有人拿着电钻,对
准我的天灵盖直接开钻。
我一个激灵坐了起来,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我嚓!
这念头刚从脑子里冒出来,我就被自己蠢哭了。
失误,绝对的失误。
我当初为了清净,特意挑了这层一梯两户的格局。签合同的时候,中介还一
个劲儿地跟我吹,说对门那套一直空着,房主在国外,短期内不会回来,楼上楼
下也没有入住的。我当时一听,乐得差点当场给他一个么么哒。
周围没人住,就意味着绝对的私密和安静。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赐的完美
工作环境。
可我他妈千算万算,算漏了一点。
这是个新楼盘!
新楼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入住率不高,也意味着随时可能有新邻居搬进来
搞装修!
「嗡——滋啦——」
那要命的电钻声又来了,这次还夹杂着切割瓷砖的尖锐噪音,跟魔音灌耳似
的,一声声往我太阳穴里钻。我感觉我那张从国外订回来的恒温水床都在跟着共
振。
我花了小十万精心打造的「情趣屋」,我引以为傲的私密王国,现在听起来
跟个建材市场没什么两样。
这还怎么做生意?
哪个男人愿意花大价钱来我这儿,一边在我身上驰骋,一边听着隔壁的交响
乐?是嫌我不够响,还是嫌他们自己不够响?
我脑子里已经有画面了。
客人刚进入状态,准备一展雄风,隔壁「咣当」一锤子下来,直接给他吓萎
了。这他妈算谁的?算工伤吗?
越想越气,我一把掀开被子,光着脚踩在地板上。一股火气从脚底板直冲天
灵盖。
去他妈的,姐姐我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想断我财路,我先让你断手断脚!
我冲到衣柜前,随手抓了件真丝睡袍披上,两步就走到门口,手刚摸到门把
手,又停住了。
不对。
就这么出去,万一对方是个不讲理的糙汉,看我穿得这么清凉,起了歹心怎
么办?虽然姐姐我不怕事,但没必要惹一身骚。
我强压下心里的火,把手从门把手上收了回来。
冷静,冷静,冲动是魔鬼。
我凑到猫眼上往外瞧。
好家伙,对门的防盗门敞得跟公共厕所似的,里面两个光着膀子的男人正干
得热火朝天。一个蹲在地上和水泥,另一个拿着电钻,对着墙壁就是一通猛干。
灰尘和噪音一起从门里涌出来。
我嫌恶地皱了皱眉。
转念一想,装修嘛,都是白天干活,晚上就收工了。我接客都在晚上,井水
不犯河水,好像……也行?
妈的,行个屁!
我晚上是「奋斗」,白天不得补觉啊!顶着两个黑眼圈,皮肤蜡黄,哪个老
板愿意花大价钱点我?我这块金字招牌还要不要了?
这帮人不是在装修,这他妈是在掘我的金矿!
我气得在客厅来回踱步,最后还是摸出手机,拨了物业的电话。
「喂,你好,江北一号物业中心。」电话那头的声音甜得发腻。
「你好,我是A 栋1701的业主,我投诉!我隔壁1702的装修噪音严重扰民,
现在是休息时间,你们管不管?」
「好的女士,我们了解了。按规定呢,工作日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
到六点是允许施工的。我们会派人去提醒一下,让他们尽量小点声。」
「尽量?什么叫尽量?我花那么多钱租这里的房子,就是为了听电钻交响乐
的?」
「抱歉女士,我们只能协调,没有执法权……」
我直接挂了电话,跟这帮和稀泥的废话,纯属浪费口水。
果然,等了十分钟,隔壁的噪音一分贝都没减小。
行,你们牛逼。
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我一晚上没吃东西,胃里空得发慌。
我烦躁地打开衣柜,那些性感的「战袍」现在看着都碍眼。我随手扒拉出一
套最不起眼的灰色运动服套上,又戴了顶鸭舌帽,把大半张脸都遮住。
就这副尊容,总不能再招蜂引蝶了吧?
结果刚到电梯口,电梯门一开,正好又撞见几个上来的装修工。
一股汗臭味和劣质烟草味扑面而来。
一个黑胖头上下打量我,那眼神黏糊糊的,嘴里还「啧」了一声。
我抬眼,冷冷地扫了他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径直走进电梯。
那眼神里的意思很明白:再看,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电梯门缓缓关上,我从门缝里看到那几个人还伸着脖子往里看,脸上挂着猥
琐的笑。
真他妈晦气!
我在楼下随便找了家早餐店,胡乱塞了点东西。一想到我那张恒温水床正在
噪音里嗡嗡作响,我就食不下咽。
快九点的时候,我磨磨蹭蹭地回到楼上。
隔壁的门关了,但「嗡嗡嗡」的声音还在,只是被门板隔着,听起来闷闷的,
更让人心烦。
一宿没睡的疲惫感终于排山倒海地涌了上来,我眼皮重得像灌了铅。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睡!
我脱了衣服,换上睡裙,把自己摔进大床上,用被子蒙住头,也想不了那么
多,呼呼大睡。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一阵「咣!咣!咣!」的砸门声把我从梦里硬生生拽了
出来。
那动静,不像是敲门,倒像是要拆了我家这扇门。
我一肚子火「噌」地就蹿上了天灵盖,这帮人还真他妈没完了?装修都干到
我家啦。
我趿拉着拖鞋冲到门口,一肚子火已经烧到了嗓子眼,酝酿了一万句国粹准
备开门就喷。
猛地拉开门,正要发作,喉咙里的话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给掐住了。
门外杵着两个男人,光着膀子,一身腱子肉被汗水和灰尘裹着,在楼道的灯
光下泛着古铜色的油光。个头都快顶到门框了,就那么站着,跟两尊门神似的。
我心里那股掀翻天灵盖的火气,瞬间被这俩人的体格给压下去三分。
一个方脸,一个横肉,看我的眼神都带着点直愣愣的冲劲。
我下意识地裹紧了身上的真丝睡袍,火气虽然降了,但脸色依旧难看:「有
事?」
那个方脸的汉子明显愣了一下,目光在我睡袍的领口和光着的腿上转了一圈,
才憨声憨气地开口:「小姐,我们……」
「小姐?」
这两个字像点燃了炸药桶,我压下去的火「噌」地又冒了三丈高。
「你他妈嘴巴放干净点!你叫谁小姐呢?」我音调陡然拔高,「你才是小姐,
你们全家都是小姐!」
我这一嗓子,整个楼道都回荡着我的余音。
另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吓了一跳,赶紧上前一步,蒲扇大的手掌一个劲儿地
摆着,脸上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哎哟,大妹子,对不住,对不住!俺哥
们儿从村里出来的,不会说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们之前不知道这屋有人,物业刚跟我们打过招呼,说吵到您了,我们这
不,机器都停了。」
我这才反应过来,难怪刚才睡得那么沉,原来是这帮人消停了。
看他态度还算诚恳,我的火气又消了七七八八,但依旧抱着胳膊,摆出一副
「老娘不好惹」的架势:「停了?停了还跑来砸我的门?不知道我在补美容觉吗?
姐姐我的青春可是无价的,耽误了你们赔?」
那横肉男搓着手,一脸的为难,都快急出汗了:「大妹子,你千万别误会,
我们不是故意的。是我们有个工友,刚才干活不小心,手让角磨机给划了,老大
一道口子,血都止不住。」
他越说越急:「这小区附近连个药店都没有,就想问问,你家……你家有没
有那个,就那个,止血的药和纱布啥的?」
他说着,我下意识地往他身后瞥了一眼。
楼道拐角的阴影里,果然蹲着个人,他用一块脏兮兮的布死死捂着手,鲜血
已经渗透了布料,正一滴一滴地砸在地上,晕开一小滩暗红。那人疼得浑身发抖,
牙关紧咬,一声不吭。
看这架势,不是装的。
我这人吧,吃软不吃硬。虽然平时脾气冲,但最见不得这种老实人受伤的场
面。
说到底,都是出来卖力气换钱的,谁又比谁高贵到哪儿去?
再说了,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俩人虽然长得凶,但好歹是低声下气地求我。
我要是「砰」地把门一摔,保不准他们记恨上,以后天天给我整点噪音听,那我
还做不做生意了?
我心里的小算盘打得飞快,脸上却依旧不动声色。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像是做了什么天大的决定,把满心的不耐烦都压了下
去。
「行了,算我倒霉。」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们一眼,大概是平时让男人进屋是
惯性动作了,就无脑说了一句,「你们俩个,跟我进来拿吧,进来赶紧关门,外
面灰大,还有拖了鞋再进」
「哎,好嘞好嘞!谢谢大妹子!你真是好人!」横肉男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如
释重负。
他们小心翼翼把沾满泥灰的解放鞋脱在门口,赤着脚,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
放,拘谨地站在我那块小小的羊毛地毯边上。
我没再搭理他们,让他们在客厅待着,自己转身进了自己的卧室,想着就是
赶紧拿药救人。
我拉开衣柜门,翻了半天也没找着。
这才想起来,那个该死的急救箱,搬家时为了省事,被我一脚塞进了床底最
里面的角落。
外面还一个流着血的可怜小哥,我心里也急,整个人趴在地上,伸长了胳膊
往黑漆漆的床底下够。
这身睡裙是真丝的,滑溜溜地贴着皮肤,我这么一趴,裙摆直接滑到了腰上。
好不容易指尖碰到了药箱的硬壳,我憋着一口气,正准备使劲把它拽出来。
就在这时,客厅里传来一阵椅子腿摩擦地面的声音,很轻,但在这安静的屋
子里,格外刺耳。
我心里一紧,抓着药箱猛地抽了出来,起身一回头,整个人都僵住了。
那两个粗狂民工,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我的卧室门口,直勾勾地盯着
我。
那个方脸的汉子,嘴巴半张着,喉结上下滚动,眼神里是没加掩饰的欲望。
另一个横肉脸的,则一个劲地咽口水,呼吸都粗重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这才反应过来。
我刚才着急,忘了身上这件粉色吊带睡裙短得可怜,只到大腿根。我刚才那
个跪趴在地上往床底掏东西的姿势……
我那没穿内衣的后背,还有只穿了条清透裤头,岂不是被他们看了个精光?
我脸上一阵燥热,瞬间又转为冰冷,抓着药箱和绷带,快步走过去,没好气
地塞到他们手里。
「拿去!赶紧走!」
那两人如梦初醒,被我一吼,脸上臊得通红,嘴里含含糊糊地道着谢,抓着
东西,几乎是落荒而逃。
听着防盗门「砰」的一声关上,我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妈的,真晦气,一分钱没花就让他俩白嫖了!」
我嘴上骂着,可心里却窜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兴奋。
我走到卧室的穿衣镜前,鬼使神差地,学着刚才的样子,慢慢跪趴下去,然
后扭过头,看向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粉色的丝质睡裙堆在腰间,整个浑圆挺翘的屁股几乎毫无遮拦。从
这个角度,甚至能隐约看到腿根处最私密的地方。
这画面,比我拍给金主看的任何一张照片都骚气。
怪不得那俩憨憨跟丢了魂儿似的。
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镜子里那副光景,连我自己都觉得烧得慌。
一个念头,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冒了出来。
刚才那两个又笨又粗的家伙,但凡胆子大上那么一分,不是落荒而逃,而是
直接把我按在床上……
我心里嗤笑一声,自己都觉得荒唐。
我叶雨楠什么场面没见过,那些西装革履的大老板,哪个不是猴急猴急的,
可偏偏玩不出什么新花样,远不如这种原始的、带着汗味的冲击来得刺激。
我坐回床上,那股莫名的燥热还在身体里窜。
我鬼使神差地,把手探进了真丝睡裙的裙摆下。
指尖触碰到温热的肌肤,我脑子里不受控制地开始回放刚才的画面。
他们俩那副想看又不敢看,口水都快流下来却又吓得跟鹌鹑似的怂样,简直
比我收过的任何一份礼物都有意思。
要是他们没走呢?
那个方脸的,会不会用他那双满是老茧的手抓住我的脚踝?那个横肉脸的,
会不会直接撕开我这身碍事的睡裙?
我呼吸渐渐急促,身体的反应远比脑子要诚实。
那两个憨货的眼神,像两把粗糙的刷子,在我光溜溜的后背上反复刮擦,留
下一片滚烫的痒。
我忍不住把手按在胸口,隔着薄薄的真丝,感受着那里的心跳,一下,又一
下,撞得我指尖发麻。另一只手,也鬼使神差地,顺着平坦的小腹,慢慢滑向腿
间。
就在我把自己绷成一张蓄势待发的弓,脑子里乱七八糟的画面快要炸开时,
门口突然又传来「咚咚」两声。
声音不大,却像两记重锤,砸得我浑身一哆嗦。
「操!」
我脱口而出,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顶到了天灵盖。还他妈的有完没完了?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气势汹汹地冲到门口,猛地拉开门,准备开喷。
门外站着的,竟然是刚才那个流血的民工小哥。
他好像刚用冷水洗了把脸,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脸上那股子窘迫和紧
张还没散干净,看见我,他咧开嘴,却露出一口小白牙,憨憨地笑着。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我憋着一肚子起床气,刚想开门骂他个狗血淋头,
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小姐姐……那个,谢谢你的药和纱布。」
他手里捏着那半卷用剩下的纱布和药膏,小心翼翼地往前递了递,眼神却飘
忽着不敢往我脸上看,只一个劲儿地盯着我脚下那块柔软的羊毛地毯。
他说话磕磕巴巴,透着一股老实人的局促。我这才仔细打量了他几眼,这人
看着好像也比我大不了多少,皮肤是常年在工地日晒下的小麦色,但五官却很周
正,特别是那双眼睛,干净得有点不像话。这种人怎么会来干这种粗活?
我顺着他的目光低头,瞥了一眼他那只举在半空中的手。纱布包得歪七扭八,
活像个新手包的粽子,边角还渗出一点血丝。
真笨。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那股无名火就这么散了。
「行了,好了就行,下次干活长点眼睛。」我懒洋洋地靠在门框上,双臂环
在胸前,丝毫没有要接他东西的意思,「剩下的你们留着吧,指不定明天谁又挂
彩了。我这可不是医药公司,不搞二次回收业务。」
我话说得冲,但语气已经不自觉地软了下来。
「哎,哎,那……那太谢谢你了!」他好像完全没听出我话里的调侃,一个
劲儿地点头,脸上的感激不似作伪,「你真是个好人!」
好人?
我差点笑出声。这年头,居然还有人给我发「好人卡」,真是新鲜。
他局促地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见我没有再开口的意思,才跟个受了惊的兔
子似的,挠了挠头,转身快步走了。
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一切。
我靠在门板上,脑子里却回想起他刚才那句「你真是个好人」。
真是个傻小哥。
我关上门,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刚才那股燥热劲儿被这么一打岔,也散得差
不多了。
回到卧室,我一屁股坐回床上,准备换掉这身惹事的睡裙。
可屁股刚一挨着床单,我就感觉不对劲。
那块地方,凉飕飕,湿漉漉的。
我挪开屁股一看,淡粉色的真丝床单上,赫然印着一小块比硬币略大的深色
水印。
我愣了两秒,随即反应过来是什么。
「我靠……」我忍不住低骂一声,又觉得好笑。
我这身子,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无奈地摇了摇头,扯下床单,扔进了洗衣机。
太阳下山,瓢泼大雨,雷声一个接一个地在头顶炸开。
微信上新加的几个好友头像闪个不停,我划拉着屏幕,像批阅奏章一样筛选
着今晚的「高端客户」。这个头像用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变态吧,下一个报价
上来就想砍一刀的,穷鬼,拉黑。
挑来拣去,总算有几个看起来人傻钱多的备选。
正准备挨个回复,手机屏幕顶端突然弹出来一条橙色预警。
「江北汛期水位告急,跨江大桥临时封锁,请市民非必要不过江、不出门。」
我操。
这几个刚勾搭上的,全住江对面。
这鬼天气,别说开车过来,就是划船都得被浪掀翻。
得,今晚算是白玩了。
空守着金山,却没个识货的来开采,这比亏钱还让人憋屈。
我无聊地刷了会儿剧,越看越烦,索性把手机扔在一边,准备洗个澡早点睡。
浴室里水汽蒸腾,热水劈头盖脸地冲下来,总算驱散了些烦闷。我刚把身上
的泡沫冲干净,头顶的浴霸灯「啪」地一下就灭了,整个世界瞬间陷入一片漆黑
和死寂。
「操。」
我低声骂了一句,摸黑裹上浴巾,趿拉着拖鞋走到门口。这破小区,线路该
不会是被雷给劈了吧?
楼道里的声控灯也瞎了,我只好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借着那点可怜的光找到
墙上的电闸箱。
一股子焦糊味都没有,不像是烧了。我踮起脚,刚要伸手去推那个小小的开
关,一股混着浓重汗臭和廉价烟草味的气息猛地从背后扑了过来。
紧接着,一只布满老茧的大手死死捂住了我的嘴,另一条胳膊像铁箍一样,
从后面拦腰抱住我,轻而易举地就把我双脚提离了地面。
我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烦。
哪个不开眼的客人,玩这么大,也不提前打声招呼。先跟我玩情景剧?
我象征性地挣扎了两下,想告诉他别太过火。可那力道越来越大,勒得我胸
口发闷,几乎喘不过气。
不对劲。
这股子蛮力,还有身上那股子汗水发酵后的馊味,可不是我像什么客人。
心一下就沉到了底,我开始真的反抗起来。可那人壮得像头牲口,我的拳打
脚踢落在他身上,跟挠痒痒似的。他一言不发,粗暴地把我往隔壁拖。
「砰」的一声,房门被从里面关死。
屋里没开灯,只有角落地上放着一盏充电的小马灯,散发着昏黄的光。我被
他扔在地上,手肘在水泥地上擦过,火辣辣地疼。
光线太暗,我眯着眼,才看清捂着我嘴的那张脸。
是那个白天来我家的大方脸。
他此刻的样子,跟白天那个局促憨厚的男人判若两人。
他胸膛剧烈地起伏,喘着粗气,一双眼睛在黑暗里冒着光,直勾勾地钉在我
身上。
我心里刚骂出一句「操」,另一个黑影就从门后绕了出来。不是白天那个横
肉脸,是个生面孔,瘦得像根竹竿,他搓着手,嘿嘿地笑着,反手就把门「咔哒」
一声锁死了。
那一声落锁,在这空旷的毛坯房里,带着回音儿。
我心里的火气瞬间被这声脆响浇灭了,这不是什么角色扮演,也不是哪个金
主的恶趣味。
这是要……
紧接着,角落里,脚手架后面,墙根的阴影里,一个,两个,三个……人影
接二连三地站了起来。他们像是从水泥墙里长出来的一样,悄无声息地围了上来。
我飞快地扫了一眼。
一个,两个,三个……加上门口那俩,整整八个。
八个男人,把我围在了中间。
我下意识地抱紧了身上唯一的遮蔽物,那条刚裹上的浴巾,故作镇定地从地
上起来。
他们虽然都围着我,除了喘着粗气,都没有人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我,那
眼神像要把我身上的浴巾烧出两个洞来。
怕?当然怕,腿肚子都在发软。但怕有什么用?我叶雨楠这暴脾气就没这两
个字,可怎么脱身呢?喊救命?这鬼天气,还打着打雷,喊破喉咙也没人听得见,
再说这栋楼也没住几个人啊。
硬拼?我这点力气,不够人家一根手指头的。
靠!我叶雨楠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可被八个浑身汗臭的民工堵在毛坯房里,
这阵仗,还真是头一遭。
角落那盏充电马灯光线昏黄,把八条人影拉得又长又扭曲,像一群从地底下
钻出来的恶鬼。
我抓着浴巾的手指关节都捏白了,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脸上却不
敢露出一丝一毫的怯意。我知道,在这种地方,对这种人,你越怕,他们就越赛
脸。
正在我们短暂对峙时,我刚要开口,一个看起来年纪最大的老头搓着手,往
前挪了半步。
「小妹妹……你,你别怕。」
他一开口,一股浓重的山东口音。
「俺们就是……就是看这暴雨下个没完,路都封了,工棚也回不去,实在是
闷得慌。寻思着,请你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老头磕磕巴巴地说着山东话,眼神躲闪。
「你放心,俺们一不图财,二不害命。」
我心里冷笑一声。
不图财,不害命,那就是图我这个人啦。
话糙理不糙,总算让我悬着的心稍稍落了地。命是能保住,可这……我什么
时候接过这种档次的活?伺候这帮浑身汗臭的糙汉,我图什么?
姐姐我一向走的可是高端路线,怎么能让这群泥腿子给便宜了。
我脑子转得飞快,盘算着怎么才能毫发无伤地脱身。
我心里正盘算着,一个粗脖子男人从人群后挤了出来,一双贼眉鼠眼的眼睛
在我身上滴溜溜地转,声音尖细,带着一股子谄媚。
「妹子,你别误会。哥哥们就是……就是听说你那屋里,弄得挺邪乎的。」
他搓着手,笑得一脸猥琐,「带我们过去开开眼呗?我们保证,就看看,就看看。」
我他妈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我那屋?我肠子都悔青了带那俩人进我家。
我那张从国外订回来的天鹅绒沙发床,那面专门为了看清每个细节的卧室天
花板镜,还有我那张宝贝得不行的恒温水床……
让他们这群连澡都不知道几天没洗的泥腿子进去?
让他们踩我铺的羊毛地毯?
我呸!
那不是糟蹋东西吗?那是我吃饭的家伙,是我的战场,我的宫殿!
没等我开骂,另一个粗狂家伙就嘿嘿笑着接了腔:「对啊妹子,听说你那床
跟水做的一样!哥哥们这辈子都没见过那样的稀罕玩意儿。」
这话一出,周围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粗俗哄笑。
我气得胸口发闷,刚想骂,一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我说老妹儿啊,你就别装了。」
我顺着声音看过去,是个穿着迷彩背心的胖哥,他冲我挤眉弄眼,「我就是
飞飞,刚加的你微信。你聊天记录里不是说,今晚寂寞,欢迎勇士来挑战吗?」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被雷劈了。
我那个专用于约客的微信小号!定位一开,附近的人都能搜到。我他妈怎么
就忘了隔壁还窝着这么一群狼!
我感觉捂着浴巾的手都在抖,不是怕的,是气的。
行啊,叶雨楠,玩了这么多年鹰,今天倒让一群土鸡给啄了眼。
我深吸一口气,反倒冷静下来了。
怕是没用的,既然身份都挑明了,那这事儿就得按「规矩」来办。
我缓缓站直了身子,故意挺了挺胸,浴巾的边缘被绷得更紧了。
我的目光冷冷地从他们八张脸上扫过,心里也开始嘀咕,于是计上心头。
行,既然都把话挑明了,姐姐我也摊牌了。
我理了理头发,抱着胳膊,下巴微微抬起,用眼角的余光扫过他们一张张冒
着油光的脸。
「玩,当然可以。」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这空旷的毛坯房里,每个字都带着
回音,「不过,得按我的规矩来。」
我伸出四根手指,指甲上新做的碎钻在昏黄的灯光下闪了一下。
「这个数,一个人,一次。先扫码,后办事。」
「四百啊……滋滋滋,我还当多钱呢」有人不屑道。
「呸,当我有多贱,四千,四千一炮」我急忙回怼。
我话音刚落,那个瘦竹竿就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尖着嗓子跳了起来:
「四千?!你抢钱啊!你那逼镶金啦!?」
他这一嗓子,像是点燃了炸药桶。
「操,四千块!俺在工地上搬一个月砖都挣不了这么多!」
「就是,太黑了!俺们在村里找个婆娘睡一宿,给二百块钱都算大方了!」
「妹子,你这价也太离谱了……」
我冷眼看着他们群情激奋,心里早就料到了。就这帮泥腿子,估计连四百块
的妞都没碰过。
一片嘈杂里,那个年纪最大的老头搓着手,又往前蹭了半步,脸上堆着不自
然的笑,试探着开口:「那个……小妹妹,你看哈,俺们这……人多。」
他嘿嘿一笑,露出一口黄牙,「现在不兴叫……叫团购嘛?能不能,给俺们
打个折?」
团购?
我他妈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直接笑出声。这老头子,还挺与时俱进。
我强忍着笑意,把胳膊抱得更紧了,胸口被挤出一道惊心动魄的弧度,故意
拖长了调子:「行啊,看在各位大哥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姐姐今天就给你们个团
购价。」
我顿了顿,伸出三根手指。
「三千。每人,一分不能少。」
「三千也贵啊!」
「是啊,够买多少斤猪肉了……」
他们又开始嗡嗡地议论起来,像一群苍蝇。
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顶到了脑门,耐心彻底告罄。我猛地把手往腰上
一插,想骂他们滚蛋。
可我忘了,我身上唯一的遮蔽物,就是那条被水浸湿后重了不少的浴巾。
这一个大动作,那本就松松垮垮系着的浴巾,再也挂不住了。
「哗啦」一声。
浴巾,顺着我光滑的皮肤,滑落在了脚边。
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
之前所有的嘈杂、抱怨、讨价还价,全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只剩下八道粗
重的呼吸声,和那盏小马灯发出的微弱电流声。
空气仿佛凝固了。
八双眼睛,像是被强力胶粘住了一样,死死地钉在我身上。
我脑子「嗡」的一声,也懵了。
也就一秒钟,我猛地反应过来,尖叫一声,闪电般地蹲下身子,捞起地上的
浴巾,胡乱地在身前一裹。脸颊烫得能煎鸡蛋,也不知道是羞的还是气的。
我抱着膝盖,也不敢站起来,就这么蹲在地上,梗着脖子吼了一句:「就三
千!爱干不干,不干滚蛋!」
死寂的房间里,响起一个男人吞咽口水的声音,格外清晰。
「唉……唉……这妹子,真他妈的白……」
「何止是白,那屁股,那大白奶……乖乖……又大又圆……」
「值了,我活了四十多年,没见过这么带劲的小娘们。三千就三千!干了!」
「对!干了!这钱花得不冤!」
我蹲在地上,听着他们越来越兴奋的议论,心里那点慌乱和羞愤,慢慢被一
种奇异的冷静所取代。
行啊,叶雨楠,姐姐我这身肉,可比任何花里胡哨的广告都管用。
最终,还是那个年纪最大的老头一跺脚,像是下了天大的决心「成!妹子,
三千就三千!俺扫码!」
「我也扫」
「我也操」
我在地上一听暗喜,要是这八个老爷们一人三千,那就是三八二十四,两万
四啊,这可比我平时一晚还大几千啊,不过又一想这帮大老粗确实有些土,哎,
算了,以前跟民工头子又不是没少干,为了钱,先忍了。
我慢慢起身「看来各位都决定的差不多了,那咱们就按照谈好的价来了」说
完,我就转身。
「哎哎!妹子你干啥去啊?价都谈好了,你咋还走?」那老头急了,伸手就
想拦。
我侧身躲开,回头瞥了他一眼,有些不耐烦:「你们有那玩意儿吗?」
「啥玩意儿?」
「套!」
「啊……哈哈哈哈」这帮老爷们大笑。
「竹竿,你,你跟着老妹去!」
我笑了,冲他们摆摆手:「我说各位大哥,心放回肚子里。价都谈完了,我
还能跑了不成?再说,这层楼就咱们这些人,大雨天我能跑到哪儿去?」
他们一听,觉得也是这个理,便没再坚持。
我假装大摇大摆地走出去,推开电闸,走回房间,「砰」地一声关上门,隔
绝了那八道灼人的视线。
房间里还残留着沐浴后的香气,我从床头柜里翻出那盒打开的杜蕾斯,捏在
手里,冰凉的塑料外壳硌着我的掌心。
关上门,房间里熟悉的香氛味道让我紧绷的神经稍稍一松。
真要开这个门?回去?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要不就这么算了,门一锁,他们八个还能把墙拆了
不成?真要砸门,我直接报警,就说民工耍流氓,看警察来了抓谁。
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报警?然后呢?警察把我跟他们一起带回所里,盘问一夜,最后再把我卖淫
的事情牵扯出来,罚款拘留?我叶雨楠可丢不起这个人。再说,就算这次躲过去,
以后呢?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帮人今天吃了瘪,明天就能在背后捅我刀子。
我在这儿好不容易攒下的小几十的高端客户,万一被他们搅黄了,我这心血
就全白费了。
换个地方,又要从头再来。
我烦躁地把那盒杜蕾斯扔回抽屉,可目光一转,又落在了洗衣机的床单上,
那上面,还留着一小块白天胡思乱想时弄湿的痕迹。
看着那痕迹,我又想起那几个粗犷的汉子,还有那手流着血的小哥,想起了
他那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干裂,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脸。
哎,说到底,都是可怜人。
我探口气再次拉开抽屉,把那盒东西拿了出来。鬼使神差地,我打开盒子,
把里面的小方块倒在床上。
一个,两个,三个……
不多不少,正好八个。
我盯着那八个小玩意儿,低低地笑出了声。
行吧,老天爷都他妈给我安排得明明白白,八个就是二万四,就算今晚开张
了,再说也是赚,不吃亏。我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心里那点疙瘩彻底解开了。
我随手抓起床上那件白天的粉色真丝睡裙套上,里面什么也没穿,这样方便,
省得一会还费劲。
深吸一口气,打开房门,重新走进了隔壁那间昏暗的毛坯房。
2025年8月7日发表于第一会所
本站首发
字数:12257
金老板这个大变态非让我们写自己被轮的经历,还说必有重赏,这招是真他
妈毒啊。
我窝在沙发上,跷着大长腿,一目十行地刷着小骚慕和小圆妹妹那两篇所谓
的「轮奸自传」,差点没把嘴里的红酒喷到电脑屏幕上。
不就是被一帮男人轮着干了吗?瞧她们写的,开篇那叫一个委屈,那叫一个
惨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贞洁烈女失身实录。
搞了半天,看到最后不也一个个爽得哼哼唧唧,找不着北了?
特别是小圆那老妹,非得把过程写得跟受刑似的,现在不也成了个小魅魔,
提起男人那点事比谁都门儿清。
就因为她们俩开了这个头,后来总有烦人的拐弯抹角地跑来问我:「楠姐,
你呢?你第一次被轮是啥体验啊?」
我能有什么感觉?
非要说第一次,那得追溯到初中。你还别不信,就是初中。不过那次真算不
上什么,就跟几个差不多大的辍学小混混瞎胡闹,毛都没长齐,懂个锤子。说是
轮,其实跟小孩过家家没区别,我当时甚至觉得有点无聊。
真正让我觉得栽了,倒霉到家的,刻骨铭心的,就要属那一刺了。
靠,要不是为了金老板那笔丰厚的赏金,这件事我宁愿烂在肚子里,带进棺
材里,这辈子都不会跟第二个人讲。
记得,大概是大二下学期吧,那时候小骚慕还在宿舍里抱着言情小说做情种
梦呢。而我,早就是道外区那片公认的头牌了,价高且活儿绝对好,点我的人能
从街头排到巷尾。
可惜,摊上个不做人的鸡头,雁过拔毛都算客气的,他那是直接把雁抓来炖
汤。我累死累活一晚上,他张嘴就抽走七成,还舔着脸说是「管理费」和「保护
费」。
保护我?上次有个客人喝多了想动粗,他妈的跑得比兔子都快。
我寻思着,这钱我自己躺着就能挣,凭什么分给他?
于是,我一脚踹了那孙子,决定单干。
当楼凤,自由,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
单干的第一步,就是找个合适的窝。
江北那个新小区,我一眼就相中了。
安保号称江北区第一,进出刷脸,陌生访客盘查得跟审犯人似的,完美。最
重要的是,入住率不高,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没人会多管闲事。
我租了个八十平的两室一厅。一室一厅怎么够用?小姐姐我自己住一间,
「上班」用一间,公私分明,这叫专业。
接下来就是砸钱。我花了几乎一半积蓄,把这地方彻彻底底改造成了我的专
属「情趣屋」。
客厅的主色调是暧昧的粉和紫,一张巨大的天鹅绒软沙发陷在中央,客人一
进来就能融入其中。次卧我自己住,没什么花哨,简单舒服就行。
真正的重头戏在主卧。
那张智能恒温水床是我托人从国外订的,光运费就够普通人一月工资了。天
花板上镶了整面的镜子,三百六十度无死角,能让任何男人在上面找回雄风的快
感。
连接着主卧的浴室,我丧心病狂地把墙敲了,换成了全透明的钢化玻璃。里
面是双人雨林花洒,水汽氤氲间,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
衣柜里更是我的军火库,各式各样的「战袍」挂得满满当当。布料少得可怜,
遮住的还没露出来的多,但效果嘛,懂的都懂。旁边的小抽屉里,手铐、眼罩、
小皮鞭……琳琅满目,能满足客人的所有幻想。
整个屋子都装了智能系统,灯光、音乐、香氛,我拿着手机就能一键切换。
想玩清纯学生妹,就来点柔光配轻音乐;想当性感女教师,那就红光配爵士乐。
看着这个完全由我掌控的王国,我心里那叫一个舒坦。去他妈的管理费,去
他妈的保护费!从今天起,老娘赚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属于我自己。
万事俱备,只欠客户上门了,嘎嘎。
而事实证明,姐姐我单干的决定英明神武。
靠着「附近的人」和我精心装点的情趣屋,我手机里的客户列表一天比一天
长,微信到账的提示音成了我最爱听的爽嗨音。
不到半个月,我就积攒了好几个出手大方的回头客,赚的钱比跟着那孙子干
半年都多。
这天早上,我刚送走一个活儿好话不多的小富二代,正美滋滋地躺在床上,
盘算着这个月能攒下多少钱。
就在这时,一阵「嗡嗡嗡」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响起,像是有人拿着电钻,对
准我的天灵盖直接开钻。
我一个激灵坐了起来,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我嚓!
这念头刚从脑子里冒出来,我就被自己蠢哭了。
失误,绝对的失误。
我当初为了清净,特意挑了这层一梯两户的格局。签合同的时候,中介还一
个劲儿地跟我吹,说对门那套一直空着,房主在国外,短期内不会回来,楼上楼
下也没有入住的。我当时一听,乐得差点当场给他一个么么哒。
周围没人住,就意味着绝对的私密和安静。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赐的完美
工作环境。
可我他妈千算万算,算漏了一点。
这是个新楼盘!
新楼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入住率不高,也意味着随时可能有新邻居搬进来
搞装修!
「嗡——滋啦——」
那要命的电钻声又来了,这次还夹杂着切割瓷砖的尖锐噪音,跟魔音灌耳似
的,一声声往我太阳穴里钻。我感觉我那张从国外订回来的恒温水床都在跟着共
振。
我花了小十万精心打造的「情趣屋」,我引以为傲的私密王国,现在听起来
跟个建材市场没什么两样。
这还怎么做生意?
哪个男人愿意花大价钱来我这儿,一边在我身上驰骋,一边听着隔壁的交响
乐?是嫌我不够响,还是嫌他们自己不够响?
我脑子里已经有画面了。
客人刚进入状态,准备一展雄风,隔壁「咣当」一锤子下来,直接给他吓萎
了。这他妈算谁的?算工伤吗?
越想越气,我一把掀开被子,光着脚踩在地板上。一股火气从脚底板直冲天
灵盖。
去他妈的,姐姐我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想断我财路,我先让你断手断脚!
我冲到衣柜前,随手抓了件真丝睡袍披上,两步就走到门口,手刚摸到门把
手,又停住了。
不对。
就这么出去,万一对方是个不讲理的糙汉,看我穿得这么清凉,起了歹心怎
么办?虽然姐姐我不怕事,但没必要惹一身骚。
我强压下心里的火,把手从门把手上收了回来。
冷静,冷静,冲动是魔鬼。
我凑到猫眼上往外瞧。
好家伙,对门的防盗门敞得跟公共厕所似的,里面两个光着膀子的男人正干
得热火朝天。一个蹲在地上和水泥,另一个拿着电钻,对着墙壁就是一通猛干。
灰尘和噪音一起从门里涌出来。
我嫌恶地皱了皱眉。
转念一想,装修嘛,都是白天干活,晚上就收工了。我接客都在晚上,井水
不犯河水,好像……也行?
妈的,行个屁!
我晚上是「奋斗」,白天不得补觉啊!顶着两个黑眼圈,皮肤蜡黄,哪个老
板愿意花大价钱点我?我这块金字招牌还要不要了?
这帮人不是在装修,这他妈是在掘我的金矿!
我气得在客厅来回踱步,最后还是摸出手机,拨了物业的电话。
「喂,你好,江北一号物业中心。」电话那头的声音甜得发腻。
「你好,我是A 栋1701的业主,我投诉!我隔壁1702的装修噪音严重扰民,
现在是休息时间,你们管不管?」
「好的女士,我们了解了。按规定呢,工作日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
到六点是允许施工的。我们会派人去提醒一下,让他们尽量小点声。」
「尽量?什么叫尽量?我花那么多钱租这里的房子,就是为了听电钻交响乐
的?」
「抱歉女士,我们只能协调,没有执法权……」
我直接挂了电话,跟这帮和稀泥的废话,纯属浪费口水。
果然,等了十分钟,隔壁的噪音一分贝都没减小。
行,你们牛逼。
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我一晚上没吃东西,胃里空得发慌。
我烦躁地打开衣柜,那些性感的「战袍」现在看着都碍眼。我随手扒拉出一
套最不起眼的灰色运动服套上,又戴了顶鸭舌帽,把大半张脸都遮住。
就这副尊容,总不能再招蜂引蝶了吧?
结果刚到电梯口,电梯门一开,正好又撞见几个上来的装修工。
一股汗臭味和劣质烟草味扑面而来。
一个黑胖头上下打量我,那眼神黏糊糊的,嘴里还「啧」了一声。
我抬眼,冷冷地扫了他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径直走进电梯。
那眼神里的意思很明白:再看,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电梯门缓缓关上,我从门缝里看到那几个人还伸着脖子往里看,脸上挂着猥
琐的笑。
真他妈晦气!
我在楼下随便找了家早餐店,胡乱塞了点东西。一想到我那张恒温水床正在
噪音里嗡嗡作响,我就食不下咽。
快九点的时候,我磨磨蹭蹭地回到楼上。
隔壁的门关了,但「嗡嗡嗡」的声音还在,只是被门板隔着,听起来闷闷的,
更让人心烦。
一宿没睡的疲惫感终于排山倒海地涌了上来,我眼皮重得像灌了铅。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睡!
我脱了衣服,换上睡裙,把自己摔进大床上,用被子蒙住头,也想不了那么
多,呼呼大睡。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一阵「咣!咣!咣!」的砸门声把我从梦里硬生生拽了
出来。
那动静,不像是敲门,倒像是要拆了我家这扇门。
我一肚子火「噌」地就蹿上了天灵盖,这帮人还真他妈没完了?装修都干到
我家啦。
我趿拉着拖鞋冲到门口,一肚子火已经烧到了嗓子眼,酝酿了一万句国粹准
备开门就喷。
猛地拉开门,正要发作,喉咙里的话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给掐住了。
门外杵着两个男人,光着膀子,一身腱子肉被汗水和灰尘裹着,在楼道的灯
光下泛着古铜色的油光。个头都快顶到门框了,就那么站着,跟两尊门神似的。
我心里那股掀翻天灵盖的火气,瞬间被这俩人的体格给压下去三分。
一个方脸,一个横肉,看我的眼神都带着点直愣愣的冲劲。
我下意识地裹紧了身上的真丝睡袍,火气虽然降了,但脸色依旧难看:「有
事?」
那个方脸的汉子明显愣了一下,目光在我睡袍的领口和光着的腿上转了一圈,
才憨声憨气地开口:「小姐,我们……」
「小姐?」
这两个字像点燃了炸药桶,我压下去的火「噌」地又冒了三丈高。
「你他妈嘴巴放干净点!你叫谁小姐呢?」我音调陡然拔高,「你才是小姐,
你们全家都是小姐!」
我这一嗓子,整个楼道都回荡着我的余音。
另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吓了一跳,赶紧上前一步,蒲扇大的手掌一个劲儿地
摆着,脸上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哎哟,大妹子,对不住,对不住!俺哥
们儿从村里出来的,不会说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们之前不知道这屋有人,物业刚跟我们打过招呼,说吵到您了,我们这
不,机器都停了。」
我这才反应过来,难怪刚才睡得那么沉,原来是这帮人消停了。
看他态度还算诚恳,我的火气又消了七七八八,但依旧抱着胳膊,摆出一副
「老娘不好惹」的架势:「停了?停了还跑来砸我的门?不知道我在补美容觉吗?
姐姐我的青春可是无价的,耽误了你们赔?」
那横肉男搓着手,一脸的为难,都快急出汗了:「大妹子,你千万别误会,
我们不是故意的。是我们有个工友,刚才干活不小心,手让角磨机给划了,老大
一道口子,血都止不住。」
他越说越急:「这小区附近连个药店都没有,就想问问,你家……你家有没
有那个,就那个,止血的药和纱布啥的?」
他说着,我下意识地往他身后瞥了一眼。
楼道拐角的阴影里,果然蹲着个人,他用一块脏兮兮的布死死捂着手,鲜血
已经渗透了布料,正一滴一滴地砸在地上,晕开一小滩暗红。那人疼得浑身发抖,
牙关紧咬,一声不吭。
看这架势,不是装的。
我这人吧,吃软不吃硬。虽然平时脾气冲,但最见不得这种老实人受伤的场
面。
说到底,都是出来卖力气换钱的,谁又比谁高贵到哪儿去?
再说了,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俩人虽然长得凶,但好歹是低声下气地求我。
我要是「砰」地把门一摔,保不准他们记恨上,以后天天给我整点噪音听,那我
还做不做生意了?
我心里的小算盘打得飞快,脸上却依旧不动声色。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像是做了什么天大的决定,把满心的不耐烦都压了下
去。
「行了,算我倒霉。」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们一眼,大概是平时让男人进屋是
惯性动作了,就无脑说了一句,「你们俩个,跟我进来拿吧,进来赶紧关门,外
面灰大,还有拖了鞋再进」
「哎,好嘞好嘞!谢谢大妹子!你真是好人!」横肉男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如
释重负。
他们小心翼翼把沾满泥灰的解放鞋脱在门口,赤着脚,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
放,拘谨地站在我那块小小的羊毛地毯边上。
我没再搭理他们,让他们在客厅待着,自己转身进了自己的卧室,想着就是
赶紧拿药救人。
我拉开衣柜门,翻了半天也没找着。
这才想起来,那个该死的急救箱,搬家时为了省事,被我一脚塞进了床底最
里面的角落。
外面还一个流着血的可怜小哥,我心里也急,整个人趴在地上,伸长了胳膊
往黑漆漆的床底下够。
这身睡裙是真丝的,滑溜溜地贴着皮肤,我这么一趴,裙摆直接滑到了腰上。
好不容易指尖碰到了药箱的硬壳,我憋着一口气,正准备使劲把它拽出来。
就在这时,客厅里传来一阵椅子腿摩擦地面的声音,很轻,但在这安静的屋
子里,格外刺耳。
我心里一紧,抓着药箱猛地抽了出来,起身一回头,整个人都僵住了。
那两个粗狂民工,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我的卧室门口,直勾勾地盯着
我。
那个方脸的汉子,嘴巴半张着,喉结上下滚动,眼神里是没加掩饰的欲望。
另一个横肉脸的,则一个劲地咽口水,呼吸都粗重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这才反应过来。
我刚才着急,忘了身上这件粉色吊带睡裙短得可怜,只到大腿根。我刚才那
个跪趴在地上往床底掏东西的姿势……
我那没穿内衣的后背,还有只穿了条清透裤头,岂不是被他们看了个精光?
我脸上一阵燥热,瞬间又转为冰冷,抓着药箱和绷带,快步走过去,没好气
地塞到他们手里。
「拿去!赶紧走!」
那两人如梦初醒,被我一吼,脸上臊得通红,嘴里含含糊糊地道着谢,抓着
东西,几乎是落荒而逃。
听着防盗门「砰」的一声关上,我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妈的,真晦气,一分钱没花就让他俩白嫖了!」
我嘴上骂着,可心里却窜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兴奋。
我走到卧室的穿衣镜前,鬼使神差地,学着刚才的样子,慢慢跪趴下去,然
后扭过头,看向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粉色的丝质睡裙堆在腰间,整个浑圆挺翘的屁股几乎毫无遮拦。从
这个角度,甚至能隐约看到腿根处最私密的地方。
这画面,比我拍给金主看的任何一张照片都骚气。
怪不得那俩憨憨跟丢了魂儿似的。
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镜子里那副光景,连我自己都觉得烧得慌。
一个念头,就这么毫无征兆地冒了出来。
刚才那两个又笨又粗的家伙,但凡胆子大上那么一分,不是落荒而逃,而是
直接把我按在床上……
我心里嗤笑一声,自己都觉得荒唐。
我叶雨楠什么场面没见过,那些西装革履的大老板,哪个不是猴急猴急的,
可偏偏玩不出什么新花样,远不如这种原始的、带着汗味的冲击来得刺激。
我坐回床上,那股莫名的燥热还在身体里窜。
我鬼使神差地,把手探进了真丝睡裙的裙摆下。
指尖触碰到温热的肌肤,我脑子里不受控制地开始回放刚才的画面。
他们俩那副想看又不敢看,口水都快流下来却又吓得跟鹌鹑似的怂样,简直
比我收过的任何一份礼物都有意思。
要是他们没走呢?
那个方脸的,会不会用他那双满是老茧的手抓住我的脚踝?那个横肉脸的,
会不会直接撕开我这身碍事的睡裙?
我呼吸渐渐急促,身体的反应远比脑子要诚实。
那两个憨货的眼神,像两把粗糙的刷子,在我光溜溜的后背上反复刮擦,留
下一片滚烫的痒。
我忍不住把手按在胸口,隔着薄薄的真丝,感受着那里的心跳,一下,又一
下,撞得我指尖发麻。另一只手,也鬼使神差地,顺着平坦的小腹,慢慢滑向腿
间。
就在我把自己绷成一张蓄势待发的弓,脑子里乱七八糟的画面快要炸开时,
门口突然又传来「咚咚」两声。
声音不大,却像两记重锤,砸得我浑身一哆嗦。
「操!」
我脱口而出,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顶到了天灵盖。还他妈的有完没完了?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气势汹汹地冲到门口,猛地拉开门,准备开喷。
门外站着的,竟然是刚才那个流血的民工小哥。
他好像刚用冷水洗了把脸,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脸上那股子窘迫和紧
张还没散干净,看见我,他咧开嘴,却露出一口小白牙,憨憨地笑着。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我憋着一肚子起床气,刚想开门骂他个狗血淋头,
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小姐姐……那个,谢谢你的药和纱布。」
他手里捏着那半卷用剩下的纱布和药膏,小心翼翼地往前递了递,眼神却飘
忽着不敢往我脸上看,只一个劲儿地盯着我脚下那块柔软的羊毛地毯。
他说话磕磕巴巴,透着一股老实人的局促。我这才仔细打量了他几眼,这人
看着好像也比我大不了多少,皮肤是常年在工地日晒下的小麦色,但五官却很周
正,特别是那双眼睛,干净得有点不像话。这种人怎么会来干这种粗活?
我顺着他的目光低头,瞥了一眼他那只举在半空中的手。纱布包得歪七扭八,
活像个新手包的粽子,边角还渗出一点血丝。
真笨。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那股无名火就这么散了。
「行了,好了就行,下次干活长点眼睛。」我懒洋洋地靠在门框上,双臂环
在胸前,丝毫没有要接他东西的意思,「剩下的你们留着吧,指不定明天谁又挂
彩了。我这可不是医药公司,不搞二次回收业务。」
我话说得冲,但语气已经不自觉地软了下来。
「哎,哎,那……那太谢谢你了!」他好像完全没听出我话里的调侃,一个
劲儿地点头,脸上的感激不似作伪,「你真是个好人!」
好人?
我差点笑出声。这年头,居然还有人给我发「好人卡」,真是新鲜。
他局促地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见我没有再开口的意思,才跟个受了惊的兔
子似的,挠了挠头,转身快步走了。
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一切。
我靠在门板上,脑子里却回想起他刚才那句「你真是个好人」。
真是个傻小哥。
我关上门,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刚才那股燥热劲儿被这么一打岔,也散得差
不多了。
回到卧室,我一屁股坐回床上,准备换掉这身惹事的睡裙。
可屁股刚一挨着床单,我就感觉不对劲。
那块地方,凉飕飕,湿漉漉的。
我挪开屁股一看,淡粉色的真丝床单上,赫然印着一小块比硬币略大的深色
水印。
我愣了两秒,随即反应过来是什么。
「我靠……」我忍不住低骂一声,又觉得好笑。
我这身子,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无奈地摇了摇头,扯下床单,扔进了洗衣机。
太阳下山,瓢泼大雨,雷声一个接一个地在头顶炸开。
微信上新加的几个好友头像闪个不停,我划拉着屏幕,像批阅奏章一样筛选
着今晚的「高端客户」。这个头像用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变态吧,下一个报价
上来就想砍一刀的,穷鬼,拉黑。
挑来拣去,总算有几个看起来人傻钱多的备选。
正准备挨个回复,手机屏幕顶端突然弹出来一条橙色预警。
「江北汛期水位告急,跨江大桥临时封锁,请市民非必要不过江、不出门。」
我操。
这几个刚勾搭上的,全住江对面。
这鬼天气,别说开车过来,就是划船都得被浪掀翻。
得,今晚算是白玩了。
空守着金山,却没个识货的来开采,这比亏钱还让人憋屈。
我无聊地刷了会儿剧,越看越烦,索性把手机扔在一边,准备洗个澡早点睡。
浴室里水汽蒸腾,热水劈头盖脸地冲下来,总算驱散了些烦闷。我刚把身上
的泡沫冲干净,头顶的浴霸灯「啪」地一下就灭了,整个世界瞬间陷入一片漆黑
和死寂。
「操。」
我低声骂了一句,摸黑裹上浴巾,趿拉着拖鞋走到门口。这破小区,线路该
不会是被雷给劈了吧?
楼道里的声控灯也瞎了,我只好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借着那点可怜的光找到
墙上的电闸箱。
一股子焦糊味都没有,不像是烧了。我踮起脚,刚要伸手去推那个小小的开
关,一股混着浓重汗臭和廉价烟草味的气息猛地从背后扑了过来。
紧接着,一只布满老茧的大手死死捂住了我的嘴,另一条胳膊像铁箍一样,
从后面拦腰抱住我,轻而易举地就把我双脚提离了地面。
我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烦。
哪个不开眼的客人,玩这么大,也不提前打声招呼。先跟我玩情景剧?
我象征性地挣扎了两下,想告诉他别太过火。可那力道越来越大,勒得我胸
口发闷,几乎喘不过气。
不对劲。
这股子蛮力,还有身上那股子汗水发酵后的馊味,可不是我像什么客人。
心一下就沉到了底,我开始真的反抗起来。可那人壮得像头牲口,我的拳打
脚踢落在他身上,跟挠痒痒似的。他一言不发,粗暴地把我往隔壁拖。
「砰」的一声,房门被从里面关死。
屋里没开灯,只有角落地上放着一盏充电的小马灯,散发着昏黄的光。我被
他扔在地上,手肘在水泥地上擦过,火辣辣地疼。
光线太暗,我眯着眼,才看清捂着我嘴的那张脸。
是那个白天来我家的大方脸。
他此刻的样子,跟白天那个局促憨厚的男人判若两人。
他胸膛剧烈地起伏,喘着粗气,一双眼睛在黑暗里冒着光,直勾勾地钉在我
身上。
我心里刚骂出一句「操」,另一个黑影就从门后绕了出来。不是白天那个横
肉脸,是个生面孔,瘦得像根竹竿,他搓着手,嘿嘿地笑着,反手就把门「咔哒」
一声锁死了。
那一声落锁,在这空旷的毛坯房里,带着回音儿。
我心里的火气瞬间被这声脆响浇灭了,这不是什么角色扮演,也不是哪个金
主的恶趣味。
这是要……
紧接着,角落里,脚手架后面,墙根的阴影里,一个,两个,三个……人影
接二连三地站了起来。他们像是从水泥墙里长出来的一样,悄无声息地围了上来。
我飞快地扫了一眼。
一个,两个,三个……加上门口那俩,整整八个。
八个男人,把我围在了中间。
我下意识地抱紧了身上唯一的遮蔽物,那条刚裹上的浴巾,故作镇定地从地
上起来。
他们虽然都围着我,除了喘着粗气,都没有人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我,那
眼神像要把我身上的浴巾烧出两个洞来。
怕?当然怕,腿肚子都在发软。但怕有什么用?我叶雨楠这暴脾气就没这两
个字,可怎么脱身呢?喊救命?这鬼天气,还打着打雷,喊破喉咙也没人听得见,
再说这栋楼也没住几个人啊。
硬拼?我这点力气,不够人家一根手指头的。
靠!我叶雨楠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可被八个浑身汗臭的民工堵在毛坯房里,
这阵仗,还真是头一遭。
角落那盏充电马灯光线昏黄,把八条人影拉得又长又扭曲,像一群从地底下
钻出来的恶鬼。
我抓着浴巾的手指关节都捏白了,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脸上却不
敢露出一丝一毫的怯意。我知道,在这种地方,对这种人,你越怕,他们就越赛
脸。
正在我们短暂对峙时,我刚要开口,一个看起来年纪最大的老头搓着手,往
前挪了半步。
「小妹妹……你,你别怕。」
他一开口,一股浓重的山东口音。
「俺们就是……就是看这暴雨下个没完,路都封了,工棚也回不去,实在是
闷得慌。寻思着,请你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老头磕磕巴巴地说着山东话,眼神躲闪。
「你放心,俺们一不图财,二不害命。」
我心里冷笑一声。
不图财,不害命,那就是图我这个人啦。
话糙理不糙,总算让我悬着的心稍稍落了地。命是能保住,可这……我什么
时候接过这种档次的活?伺候这帮浑身汗臭的糙汉,我图什么?
姐姐我一向走的可是高端路线,怎么能让这群泥腿子给便宜了。
我脑子转得飞快,盘算着怎么才能毫发无伤地脱身。
我心里正盘算着,一个粗脖子男人从人群后挤了出来,一双贼眉鼠眼的眼睛
在我身上滴溜溜地转,声音尖细,带着一股子谄媚。
「妹子,你别误会。哥哥们就是……就是听说你那屋里,弄得挺邪乎的。」
他搓着手,笑得一脸猥琐,「带我们过去开开眼呗?我们保证,就看看,就看看。」
我他妈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我那屋?我肠子都悔青了带那俩人进我家。
我那张从国外订回来的天鹅绒沙发床,那面专门为了看清每个细节的卧室天
花板镜,还有我那张宝贝得不行的恒温水床……
让他们这群连澡都不知道几天没洗的泥腿子进去?
让他们踩我铺的羊毛地毯?
我呸!
那不是糟蹋东西吗?那是我吃饭的家伙,是我的战场,我的宫殿!
没等我开骂,另一个粗狂家伙就嘿嘿笑着接了腔:「对啊妹子,听说你那床
跟水做的一样!哥哥们这辈子都没见过那样的稀罕玩意儿。」
这话一出,周围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粗俗哄笑。
我气得胸口发闷,刚想骂,一个声音又响了起来。
「我说老妹儿啊,你就别装了。」
我顺着声音看过去,是个穿着迷彩背心的胖哥,他冲我挤眉弄眼,「我就是
飞飞,刚加的你微信。你聊天记录里不是说,今晚寂寞,欢迎勇士来挑战吗?」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被雷劈了。
我那个专用于约客的微信小号!定位一开,附近的人都能搜到。我他妈怎么
就忘了隔壁还窝着这么一群狼!
我感觉捂着浴巾的手都在抖,不是怕的,是气的。
行啊,叶雨楠,玩了这么多年鹰,今天倒让一群土鸡给啄了眼。
我深吸一口气,反倒冷静下来了。
怕是没用的,既然身份都挑明了,那这事儿就得按「规矩」来办。
我缓缓站直了身子,故意挺了挺胸,浴巾的边缘被绷得更紧了。
我的目光冷冷地从他们八张脸上扫过,心里也开始嘀咕,于是计上心头。
行,既然都把话挑明了,姐姐我也摊牌了。
我理了理头发,抱着胳膊,下巴微微抬起,用眼角的余光扫过他们一张张冒
着油光的脸。
「玩,当然可以。」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这空旷的毛坯房里,每个字都带着
回音,「不过,得按我的规矩来。」
我伸出四根手指,指甲上新做的碎钻在昏黄的灯光下闪了一下。
「这个数,一个人,一次。先扫码,后办事。」
「四百啊……滋滋滋,我还当多钱呢」有人不屑道。
「呸,当我有多贱,四千,四千一炮」我急忙回怼。
我话音刚落,那个瘦竹竿就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尖着嗓子跳了起来:
「四千?!你抢钱啊!你那逼镶金啦!?」
他这一嗓子,像是点燃了炸药桶。
「操,四千块!俺在工地上搬一个月砖都挣不了这么多!」
「就是,太黑了!俺们在村里找个婆娘睡一宿,给二百块钱都算大方了!」
「妹子,你这价也太离谱了……」
我冷眼看着他们群情激奋,心里早就料到了。就这帮泥腿子,估计连四百块
的妞都没碰过。
一片嘈杂里,那个年纪最大的老头搓着手,又往前蹭了半步,脸上堆着不自
然的笑,试探着开口:「那个……小妹妹,你看哈,俺们这……人多。」
他嘿嘿一笑,露出一口黄牙,「现在不兴叫……叫团购嘛?能不能,给俺们
打个折?」
团购?
我他妈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直接笑出声。这老头子,还挺与时俱进。
我强忍着笑意,把胳膊抱得更紧了,胸口被挤出一道惊心动魄的弧度,故意
拖长了调子:「行啊,看在各位大哥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姐姐今天就给你们个团
购价。」
我顿了顿,伸出三根手指。
「三千。每人,一分不能少。」
「三千也贵啊!」
「是啊,够买多少斤猪肉了……」
他们又开始嗡嗡地议论起来,像一群苍蝇。
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顶到了脑门,耐心彻底告罄。我猛地把手往腰上
一插,想骂他们滚蛋。
可我忘了,我身上唯一的遮蔽物,就是那条被水浸湿后重了不少的浴巾。
这一个大动作,那本就松松垮垮系着的浴巾,再也挂不住了。
「哗啦」一声。
浴巾,顺着我光滑的皮肤,滑落在了脚边。
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
之前所有的嘈杂、抱怨、讨价还价,全都在这一刻戛然而止。只剩下八道粗
重的呼吸声,和那盏小马灯发出的微弱电流声。
空气仿佛凝固了。
八双眼睛,像是被强力胶粘住了一样,死死地钉在我身上。
我脑子「嗡」的一声,也懵了。
也就一秒钟,我猛地反应过来,尖叫一声,闪电般地蹲下身子,捞起地上的
浴巾,胡乱地在身前一裹。脸颊烫得能煎鸡蛋,也不知道是羞的还是气的。
我抱着膝盖,也不敢站起来,就这么蹲在地上,梗着脖子吼了一句:「就三
千!爱干不干,不干滚蛋!」
死寂的房间里,响起一个男人吞咽口水的声音,格外清晰。
「唉……唉……这妹子,真他妈的白……」
「何止是白,那屁股,那大白奶……乖乖……又大又圆……」
「值了,我活了四十多年,没见过这么带劲的小娘们。三千就三千!干了!」
「对!干了!这钱花得不冤!」
我蹲在地上,听着他们越来越兴奋的议论,心里那点慌乱和羞愤,慢慢被一
种奇异的冷静所取代。
行啊,叶雨楠,姐姐我这身肉,可比任何花里胡哨的广告都管用。
最终,还是那个年纪最大的老头一跺脚,像是下了天大的决心「成!妹子,
三千就三千!俺扫码!」
「我也扫」
「我也操」
我在地上一听暗喜,要是这八个老爷们一人三千,那就是三八二十四,两万
四啊,这可比我平时一晚还大几千啊,不过又一想这帮大老粗确实有些土,哎,
算了,以前跟民工头子又不是没少干,为了钱,先忍了。
我慢慢起身「看来各位都决定的差不多了,那咱们就按照谈好的价来了」说
完,我就转身。
「哎哎!妹子你干啥去啊?价都谈好了,你咋还走?」那老头急了,伸手就
想拦。
我侧身躲开,回头瞥了他一眼,有些不耐烦:「你们有那玩意儿吗?」
「啥玩意儿?」
「套!」
「啊……哈哈哈哈」这帮老爷们大笑。
「竹竿,你,你跟着老妹去!」
我笑了,冲他们摆摆手:「我说各位大哥,心放回肚子里。价都谈完了,我
还能跑了不成?再说,这层楼就咱们这些人,大雨天我能跑到哪儿去?」
他们一听,觉得也是这个理,便没再坚持。
我假装大摇大摆地走出去,推开电闸,走回房间,「砰」地一声关上门,隔
绝了那八道灼人的视线。
房间里还残留着沐浴后的香气,我从床头柜里翻出那盒打开的杜蕾斯,捏在
手里,冰凉的塑料外壳硌着我的掌心。
关上门,房间里熟悉的香氛味道让我紧绷的神经稍稍一松。
真要开这个门?回去?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要不就这么算了,门一锁,他们八个还能把墙拆了
不成?真要砸门,我直接报警,就说民工耍流氓,看警察来了抓谁。
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报警?然后呢?警察把我跟他们一起带回所里,盘问一夜,最后再把我卖淫
的事情牵扯出来,罚款拘留?我叶雨楠可丢不起这个人。再说,就算这次躲过去,
以后呢?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帮人今天吃了瘪,明天就能在背后捅我刀子。
我在这儿好不容易攒下的小几十的高端客户,万一被他们搅黄了,我这心血
就全白费了。
换个地方,又要从头再来。
我烦躁地把那盒杜蕾斯扔回抽屉,可目光一转,又落在了洗衣机的床单上,
那上面,还留着一小块白天胡思乱想时弄湿的痕迹。
看着那痕迹,我又想起那几个粗犷的汉子,还有那手流着血的小哥,想起了
他那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干裂,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脸。
哎,说到底,都是可怜人。
我探口气再次拉开抽屉,把那盒东西拿了出来。鬼使神差地,我打开盒子,
把里面的小方块倒在床上。
一个,两个,三个……
不多不少,正好八个。
我盯着那八个小玩意儿,低低地笑出了声。
行吧,老天爷都他妈给我安排得明明白白,八个就是二万四,就算今晚开张
了,再说也是赚,不吃亏。我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心里那点疙瘩彻底解开了。
我随手抓起床上那件白天的粉色真丝睡裙套上,里面什么也没穿,这样方便,
省得一会还费劲。
深吸一口气,打开房门,重新走进了隔壁那间昏暗的毛坯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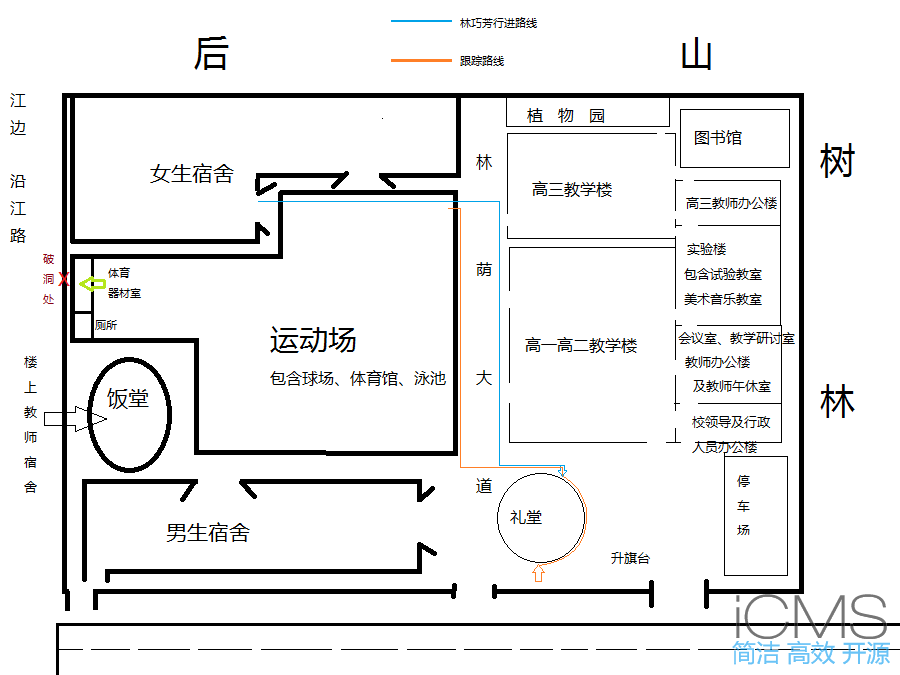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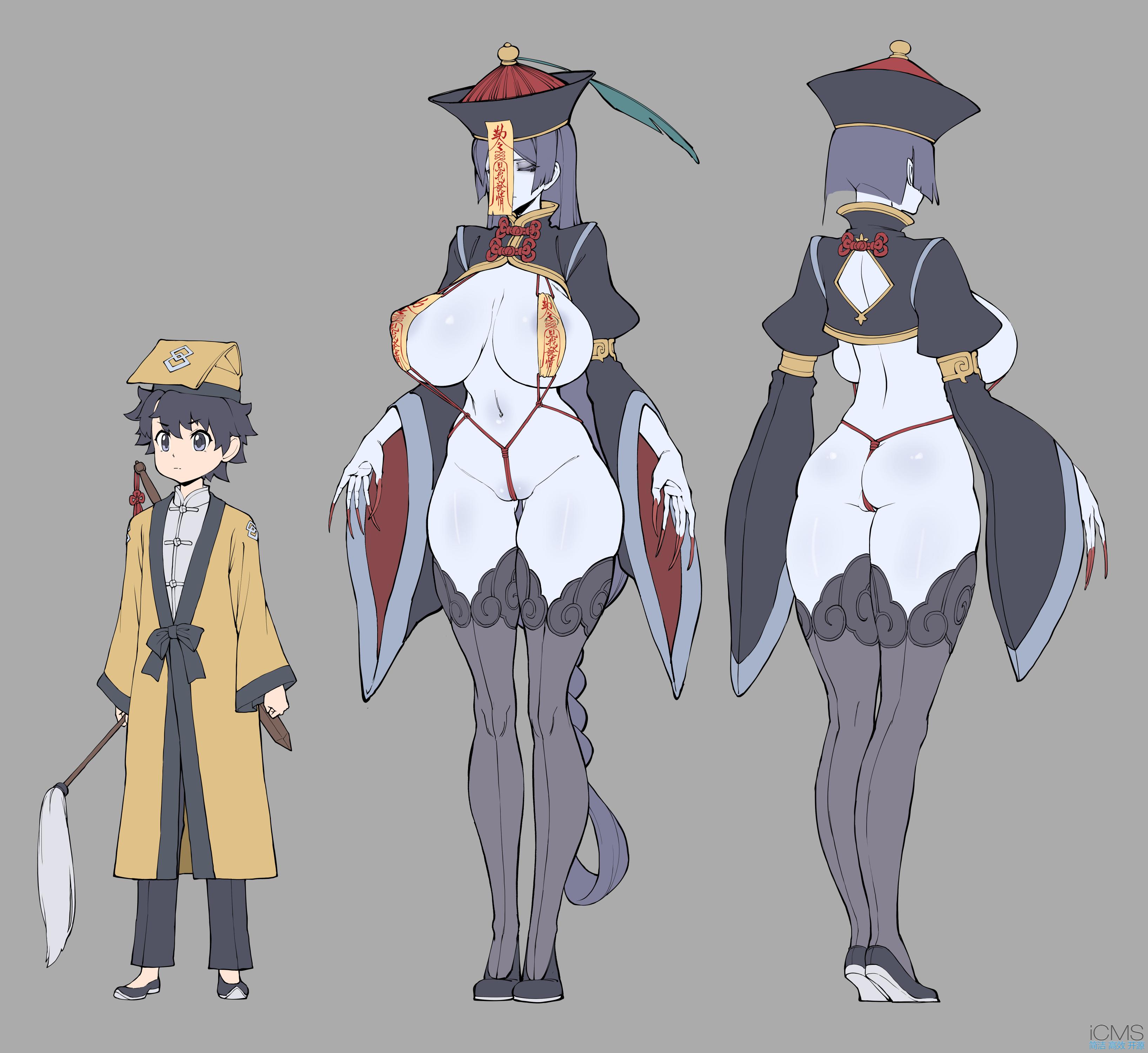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